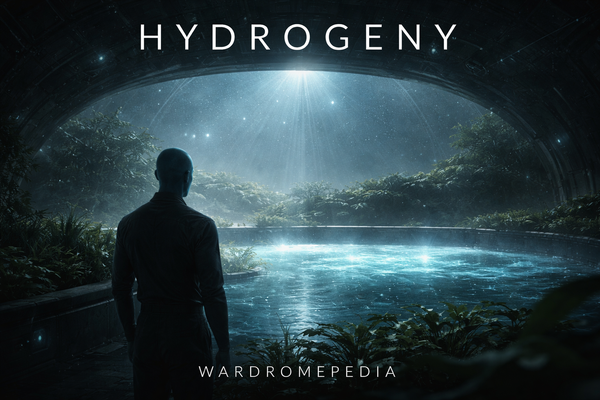游戏设计中的电影导演:从电影拍摄现场到Wardrome的RIDLEY
作为一名电影专业人士,我曾担任过多种角色——从剪辑和摄影到助理导演和第二组导演——参与了多部独立制作的作品。在转向游戏开发时,我利用这些电影经验来指导我们如何创作互动故事。在本文中,我将探讨经典的导演原则如何适用于视频游戏设计,特别是在系统性和程序性叙事方面。我还将分享我们如何通过RIDLEY在Wardrome中实施这些原则,RIDLEY是我们游戏中的“隐形导演”AI,动态地编排玩家的体验。
为什么电影原则在游戏中重要
游戏开发者长期以来借鉴电影的技巧,以增强沉浸感和情感冲击。然而,与电影导演不同,游戏的“导演”(无论是人类还是AI)必须在互动媒介中工作,其中观众也是一个积极参与者。挑战在于提供电影时刻和叙事而不剥夺玩家的主动权。
RIDLEY通过观察玩家行为并实时调整游戏事件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像Valve著名的AI导演在Left 4 Dead中一样,它监控玩家并动态生成敌人或提供喘息机会以维持节奏。目标是将电影导演与玩家响应设计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感觉既像电影又对每次游戏体验都很个人化的体验。
下面,我们将分解关键的导演原则——视觉构图、节奏、视角、情感框架、环境叙事和剪辑/蒙太奇——描述它们在电影中的作用,看看顶级游戏如何使用它们,并展示RIDLEY如何在Wardrome中利用每一个原则。
视觉构图:构建视角
在电影中,视觉构图是安排画面中元素的艺术——演员、灯光、布景设计、摄像角度——以无言传达意义。一个构图良好的镜头引导观众的视线,突出故事元素,并唤起情感(考虑韦斯·安德森电影中的平衡对称与保罗·格林格拉斯动作场景中的混乱构图)。电影制作人使用三分之一法则、引导线和前景/背景分层等技巧来创造视觉上吸引人且主题共鸣的镜头。
在游戏中:游戏设计师对构图的控制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因为玩家通常控制“相机”或视角。在许多游戏中,视角要么是固定的(例如,横向卷轴游戏),要么是玩家控制的(3D中的自由相机)。尽管如此,开发者通过环境和相机设计实现电影般的构图。例如,Playdead的Inside(2016)是一款使用固定侧视的2.5D平台游戏——但每个场景都经过精心构图,鲜明的灯光和深度创造出引人注目的轮廓。
结果感觉就像是一系列精心构图的电影镜头。评论家指出Inside的“引人深思的场景”以拉长的安静和视觉叙事的方式使用,“大胆地让玩家填补空白以赋予意义,”而这种明显的阐述只会破坏效果。
在The Last of Us(2013)中,肩上视角的第三人称相机在对话时故意保持紧凑,模拟浅景深镜头以引导我们的注意力和同情心到他们的面部表情。
即使是完全3D的游戏也使用关卡几何和相机提示来构建景观:在Shadow of the Colossus中走上悬崖会揭示出全景视图,微小的主角与巨大的景观形成对比——这种构图强调了孤独英雄在广阔世界中的主题。
Wardrome并不是因为相机技巧或视觉奇观而显得电影化。它之所以电影化,是因为它被构建为一系列有指导性的情境。RIDLEY的行为并不像虚拟摄影师,而更像是一位电视时代的导演和故事编辑,更接近于星际迷航:原始系列而非现代大片的舞台。它的核心单元不是“镜头”,而是任务:一个求救信号,一个外交事件,一个意外的遭遇,角色之间的紧张交流。
RIDLEY根据上下文、玩家状态和叙事压力组装和排序这些情境。一个任务可能以平静的传输开始,通过对话和道德紧张升级,并在没有一枪发出的情况下解决。视觉呈现仍然是次要和功能性的;重要的是谁在说话,什么是关键,以及玩家何时被迫做出决定。电影质量源于节奏、对话时机和后果,而不是视觉效果。
由于系统是程序性的,相同的叙事结构可以在不同的游戏过程中产生截然不同的情节。两个玩家可能都接到求救信号,但来自不同的派系,在不同的政治条件下,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RIDLEY并不构图图像,它指导情节。它确保Wardrome感觉像是一部活生生的科幻系列,每个会话都是一个创作的章节,即使没有固定的剧本。
节奏与韵律:把握体验的时机
节奏——叙事中的时机和韵律控制——是导演的基石。一位优秀的导演调节紧张与释放:考虑一下惊悚片如何在安静的对话场景与爆发的动作之间交替,或者戏剧如何在高潮后停留在一个沉默的情感时刻。在电影中,节奏通过剪辑、场景长度和剧本结构来控制。导演故意把握故事的节奏,以引导观众的情感旅程(希区柯克曾将悬念比作“像演奏乐器一样操控观众”,建立和释放紧张感)。
在游戏中:节奏独特而棘手,因为玩家可以停留或匆忙,可能会打乱精心计划的时机。尽管如此,游戏设计师使用各种技巧来强制或鼓励节奏。线性动作游戏(例如使命召唤系列)通常使用脚本触发器——游戏等待你达到一个隐形的检查点,然后一系列事件随之而来。这确保了一致的节奏(尽管牺牲了重玩的惊喜)。
其他游戏给予玩家自由,但使用动态难度或AI“导演” 来控制挑战的节奏。Valve的Left 4 Dead(2008)在这方面开创了先河,其AI导演:如果玩家轻松过关,它可能会生成额外的敌人以增强强度;如果他们在挣扎,它可能会暂时放松并给予喘息机会。结果是一个感觉自然且响应玩家的紧张过山车。
The Last of Us在更具剧本性的方式中巧妙地使用节奏——在一次惊险的战斗序列后,游戏通常会给你一个平静的探索环节,角色们聊天,玩家在安静中搜刮。这种潮起潮落使情感旅程不会让玩家感到压倒,并使强烈的时刻更加深刻。
在实验方面,小岛秀夫的死亡搁浅(2019)拥抱了缓慢:长时间的孤独徒步旅行,几乎没有动作,偶尔被危险或感人的过场动画打断。许多玩家发现这不寻常,但这是一个故意的节奏决定,以唤起孤独和解脱——在游戏形式中非常“导演式的”举动。
RIDLEY的方式:节奏可能是RIDLEY的主要指令。作为一个“无形导演”,RIDLEY监控着玩家的行为和表现。玩家是否在毫无挑战中轻松前进?RIDLEY可能会通过生成新的敌人遭遇或触发意想不到的故事事件来提升紧张感。玩家是否刚刚侥幸在一场艰难的战斗中幸存下来?RIDLEY会识别这一点,并暂时不再施加新威胁,也许会触发一段宁静的音乐或与友好的NPC相遇,让他们喘口气。
从本质上讲,RIDLEY动态调整游戏和故事的节奏——就像一个人类地下城主调整D&D会话。这也扩展到叙事节奏:如果玩家在没有任何情节发展的情况下走了很长时间,RIDLEY可以注入一个程序生成的故事(例如,一个引导到短小支线故事的求救信号),以保持叙事的动量。通过实时控制节奏,RIDLEY防止了令人畏惧的“中期游戏低迷”或节奏死区。游戏的流程适应玩家,旨在实现那种从开始到结束都能保持玩家参与的电影般的起伏平衡。
视角:我们通过谁的眼睛(或镜头)在看?
电影中的视角(POV)指的是观众体验场景的视角。导演决定是通过特定角色的视角(字面上的POV镜头或肩上视角)展示事件,还是通过客观的第三人称镜头。改变视角可以显著改变观众的感受——想象一部恐怖电影,我们通过怪物的眼睛看到的场景与从一个超然的视角观看受害者的场景。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第一人称视角可以创造亲密感或恐惧,而更广泛的第三人称视角可以建立背景或宏伟感。
在游戏中:视角实际上是内置于游戏玩法中的——每个游戏都有一个默认的玩家视角(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横向卷轴、等轴测等),这是一个影响游戏玩法和叙事的设计决策。
例如,生化危机7转向第一人称以增强恐怖感,提供沉浸式、幽闭的视角,而战神(2018)选择了肩上视角的第三人称,采用“一镜到底”的连续镜头,以保持与主角的亲密感和电影化的表现。
重要的是,游戏设计师在控制与沉浸之间进行权衡:与电影不同,一旦让玩家控制镜头,就放弃了精确的构图。正如一项设计分析所指出的,“游戏并不通过导演的镜头控制来聚焦你的视野,也不坚持某种节奏;相反,它们邀请你走进空间并以自己的节奏探索。”尽管如此,游戏仍然可以借用视角技巧。Inside本质上是一个长长的侧视追踪镜头——一种刻意的、创作的视角,让玩家感觉自己是一个黑暗寓言的观察者,从而增强其影响力。
最后的生还者在游戏玩法和过场动画中频繁使用肩上视角,以情感上将我们与乔尔或艾莉的视角紧密相连。与此同时,死亡搁浅在玩家控制的第三人称探索和导演控制的过场动画之间交替,科贾马使用在游戏中永远看不到的镜头角度——在叙事节奏到来时有效地将视角从玩家切换到讲述者。
RIDLEY的方式:
在Wardrome中,视角不是由镜头位置定义的,而是由在特定时刻具有叙事相关性的角色决定的。RIDLEY并不通过电影镜头移动或过场动画来改变视角;相反,它重新分配信息和情感的焦点。视角的变化通过对话优先级、信息框架、界面强调和事件顺序来表达,而不是通过视觉奇观。
当发生重大事件时,例如检测到未知船只或外交事件,RIDLEY可能会暂时优先考虑特定视角:一名桥梁官员报告不完整信息,或一名平民传输打破协议,或者一名NPC通过自己的偏见解读事件。玩家体验到的情况正是该角色理解的情况,通常伴随着不确定性或扭曲。除非已经获得,否则不会提供全知的视角。
类似地,像求救信号或直接对话这样的通信并不被视为电影插入,而是作为叙事时刻处理。RIDLEY决定谁先发言,哪些信息被延迟,哪些情感基调主导交流,以及何时沉默比阐述更有意义。结果是一个认知而非视觉的视角转变:玩家被鼓励从一个视角内部思考,而不是从外部观察。
这种方法在保持玩家主动性的同时,仍然应用导演意图。RIDLEY并不“展示”玩家该感受什么;它限制和框定可以被知道的内容,就像经典的分集科幻电视节目一样。电影效果源于视角控制和叙事时机,确保Wardrome中的每个情况都传达出正确的紧迫感、模糊性或范围,而不会打破互动流程。
情感框架:设定情绪和基调
导演本质上是情感管理者——通过构图、照明、音乐和演员表现,他们情感上框定每一个时刻,让观众感受到他们所意图的情感。“情感框架”在电影中可能涉及使用特写镜头捕捉角色泪水盈眶的眼睛(以唤起同情),在温暖的日落色调中拍摄场景(以创造怀旧或浪漫),或构图一幅孤独身影在广阔空旷景观中的宽镜头(以传达孤立或敬畏)。框架中的所有元素都服务于情感基调。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斯皮尔伯格在E.T.中使用低角度镜头和激昂音乐,当自行车起飞时——构图和音频提示观众感受到惊奇和快乐。相比之下,恐怖片使用紧凑的构图和大量阴影来创造焦虑。导演还控制节奏和演员的阻挡,作为情感框架的一部分(例如,缓慢推进的镜头移动可以建立恐惧或亲密感)。
在游戏中:游戏通过叙事/电影和游戏反馈来激发情感。视觉和音频设计至关重要:色彩调色板、照明和音乐动态变化以反映游戏状态(想想寂静岭如何将你包围在雾气和诡异的收音机静电中以灌输恐惧,或旅程如何利用广阔的沙漠景观和管弦乐曲调来激发敬畏和忧伤)。
值得注意的是,游戏通常必须实时执行此操作,以响应玩家的行为。最后的生还者再次是一个大师级的例子——其视觉和音效设计共同“传达情感的弧线”,确保所有元素——从褪色、腐朽的环境到令人难忘的配乐——与每一章的基调相一致。即使在纯粹的游戏玩法中,机制也可以框定情感:高难度的战斗可以创造绝望和胜利,宽松的和平区域则带来解脱。
死亡搁浅值得一提的是其情感框架:小岛秀夫故意让景观荒凉而敌对,但有时游戏会触发一首低吼的歌曲,并在你越过山丘时将镜头拉出到电影般的广角镜头——这是一个有指导性的情感反思时刻,让玩家感到渺小和孤独,但又充满希望地重新连接这个破碎的世界。这些技巧反映了电影,但有一个转折:互动性。与被动观众不同,玩家自己的输入(如艰难攀登山路)有助于情感框架——当音乐响起时,游戏可能会减缓角色的移动并移除HUD元素,从而本质上将游戏玩法本身框定在情感的光芒中。
RIDLEY的方法:
在《Wardrome》中,情感框架不是通过视觉效果或电影表现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背景、语气和叙事压力。RIDLEY并不通过改变灯光或音乐提示来“营造气氛”;相反,它调节玩家被告知的内容、何时被告知以及在什么情感条件下做出决策。
RIDLEY不断评估故事的状态和玩家在其中的位置。即将失败的情况可能通过碎片化的报告、犹豫的对话、NPC的矛盾建议或明显缺乏安慰信息来框定。相反,成功或联盟的时刻可能因不安、模糊或延迟的后果而被削弱,而不是明显的庆祝。《Wardrome》中的情感框架很少是明确的;它通常是推断出来的,迫使玩家与不确定性共处,而不是被引导向一种规定的感觉。
程序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RIDLEY将叙事状态与对话语气、任务结构和信息可靠性的变化联系起来。背叛并不需要戏剧性的揭示;它可能通过微妙的不一致、改变的优先级或角色如何称呼玩家的突然变化浮现出来。情感的重量来自于积累和时机,而不是呈现。
这种方法反映了技术娴熟的电影导演通过克制而非强调所实现的效果。RIDLEY通过控制叙事访问来施加情感引导,而不是通过放大信号。因此,《Wardrome》保持情感响应而不变得操控:紧张、怀疑、释然或决心自然地从玩家与系统的互动中产生。故事之所以感觉生动,并不是因为它告诉玩家该如何感受,而是因为它不断将玩家置于不可避免的情感情境中。
环境叙事:世界作为角色
在电影中,制作设计和布景往往在任何角色说话之前就讲述了一个故事。术语环境叙事指的是通过环境本身传达叙事。导演可能会在背景中展示一面满是家庭照片的墙壁,以暗示角色的历史,或在反乌托邦的城市景观中停留在涂鸦上,以暗示社会的崩溃。经典的例子包括机器人总动员开头的废弃杂物(大量讲述失落的人类世界)或异形中阴森的、居住过的诺斯特罗莫号,它通过细节告诉你这是一个在太空中运作的工人阶级货运操作。
在游戏中:环境叙事可以说甚至更为重要,因为玩家花费大量时间探索世界。一个设计良好的游戏环境可以在没有任何过场动画或文本的情况下暗示事件或背景故事——让玩家自然而然地发现故事片段。
生化危机(2007)经常被引用:水下城市拉普彻充满了视觉线索(褪色的装饰艺术辉煌、暴力崩溃的迹象、音频日记),让玩家拼凑出发生了什么。
最后的生还者以令人心碎的效果使用这一点:你常常会偶然发现一些场景,比如靠在墙上的骷髅,旁边是一张家庭照片和一封未写完的便条——从这些环境细节中,你推断出在感染爆发期间一个家庭的悲惨最后时刻。无需过场动画;玩家填补空白,使发现变得个人化和深刻。这种微妙的“暗示叙事”鼓励玩家充当侦探,通过解读线索共同创作故事。
Playdead的Inside和Limbo也是很好的例子——几乎一切你对情节和世界的理解都来自于景观及其变化(阴森的实验室、被控制的僵尸等),没有任何对话。环境叙事不仅仅是背景故事;它还可以指导游戏玩法。设计师在关卡中使用因果关系小插曲(一条通往门口的血迹暗示着前方的危险)或地标(远处的塔楼帮助玩家定位)——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环境讲述的故事。
RIDLEY的方法:
在《Wardrome》中,环境叙事并不是静态道具的摆放,而是叙事情境的语境化。由于地点、叙述和对话都是动态生成的,RIDLEY并不“装饰”环境;它赋予它们意义。一个地方通过关于它的叙述、发生的事情以及角色如何解读它而变得叙事相关。
当玩家被派往一个废弃的空间站时,RIDLEY并不单靠预先编写的环境线索。相反,它围绕该地点构建一个连贯的叙事框架:描述部分失败的报告、来自不同来源的矛盾证词、碎片化的日志或在简报期间的不安沉默。任何出现的环境细节,无论是物理的还是描述性的,都是为了加强该框架而选择的。环境是为叙事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
同样,事件的后果不是通过壮观的场面传达的,而是通过叙事残留。如果一个殖民地被攻击或遗弃,RIDLEY确保后续的任务、对话和报告反映这一结果。稍后的访问可能伴随着改变的简报、NPC的态度变化或对失去的事物的二手描述。一个地方的“废墟”往往在对话和叙述中重建,而不是明确展示,让玩家的想象力来完成画面。
至关重要的是,RIDLEY跟踪玩家的决策,并在游戏的叙事结构中传播其影响。忽视求救信号并不会立即触发可见的失败状态;相反,其后果通过谣言、改变的任务可用性或政治关系的变化逐渐浮现。因此,环境叙事变得时间性和关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展开,而不是在单一地点被消耗。
在这个模型中,《Wardrome》的银河系之所以感觉生动,并不是因为它装饰得很密集,而是因为它被持续叙述。每个地方都由已知的、不确定的和被记住的内容定义。通过确保叙述、对话和任务背景与过去事件保持一致,RIDLEY允许玩家发现一个庞大、相互关联的故事世界,这个世界是动态组装的,但体验上却是有意图和有作者的。
编辑与蒙太奇:剪辑、过渡和叙事流
编辑——将镜头组合成序列——是电影叙事背后的无形艺术。通过剪辑、蒙太奇和过渡,导演控制叙事结构、压缩时间,并通过图像的并置传达意义。快速的蒙太奇可以在几秒钟内涵盖数年的故事;突然剪接可以带来震惊或笑声;交叉剪接可以通过交织两个线索来建立悬念。归根结底,编辑是电影真正成为故事的地方。观众在屏幕上看不到编辑的工作,但他们在叙事的节奏和连贯性中感受到它。
在游戏中:传统的编辑(从一个镜头切换到另一个镜头)在互动游戏中并不常用——你不能随意切换玩家的视角而不让他们感到迷失。游戏主要在非互动的过场动画中使用编辑,这些过场动画往往完全模仿电影编辑。
例如,神秘海域和最后的生还者有许多过场动画,其中包含镜头反转对话、旅行的蒙太奇(以跳过无聊部分)等,和电影一样。然而,游戏也使用互动的编辑等价物。考虑那些让你触发“跳过旅行”的游戏——这本质上是一个蒙太奇或时间的剪接,由玩家选择执行。
一些游戏在游戏玩法中采用了蒙太奇序列(例如,睡狗中的训练蒙太奇通过一系列迷你游戏和过场动画片段进行)。
荒野大镖客2在你骑马穿越城镇时无缝过渡到电影镜头和音乐,有效地编辑掉了乏味的部分,并将旅行呈现为带有情感音乐的蒙太奇。
还有动态叙事序列的概念:在底特律:变人中,场景可以根据选择重新排列或跳过——故事序列的“编辑”部分由玩家决定,但游戏确保它仍然逻辑流畅。
一个关键的设计准则是,虽然电影说“展示,而不是叙述”,游戏则说“做,而不是展示”。
正如《波斯王子》创作者乔丹·梅赫纳所说,“在电影中,展示比叙述更好,但在视频游戏中,做比观看更好。把故事中最精彩的时刻给玩家,他永远不会忘记——放在过场动画中,他会打哈欠。”
这概括了挑战:游戏不应该过于依赖非互动的过场动画编辑来呈现它们的最佳时刻。相反,游戏中一些最强大的“编辑”是玩家创造的——例如,在我的世界中,当玩家在夜幕降临时建造庇护所时,实际上是玩家通过行动而不是镜头编辑出自己的生存故事。
RIDLEY的方法:
在Wardrome中,编辑并不是关于剪切图像或插入非互动序列。它是关于决定情况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以及它们如何相互跟随。RIDLEY不会通过过场动画或蒙太奇打断游戏玩法;相反,它执行可以被描述为叙事编辑:对时间、焦点和故事进展的调节。
RIDLEY通过在适当时推进或压缩叙事时间来控制节奏。如果玩家在预定发展之前耗尽了所有有意义的行动,系统可能会隐性推进时间线,让后果展开而不需要玩家闲置。时间的流逝不是通过视觉设备,而是通过更新报告、改变任务可用性或新信息进入叙事空间来实现的。电影用溶解或蒙太奇解决的问题,Wardrome通过状态转换来解决。
平行故事线以类似的方式处理。Wardrome可能包含多个活跃的叙事线索,政治、个人或战略的,所有这些都以不同的速度发展。RIDLEY监控它们的叙事权重,并在不平衡出现时进行干预。如果主要冲突主导了太长时间,RIDLEY可能通过意外消息、干预请求或角色行为的变化重新引入次要线索。这不是电影意义上的剪接,而是叙事注意力的重新分配,可比作节目制作人决定何时浮现一个子情节以保持整体连贯性。
至关重要的是,这些过渡从来不是任意的。RIDLEY仅在改善清晰度、节奏或后果时进行干预。重复不是通过删除而是通过升级或解决来最小化。叙事重要性的时刻被允许共鸣,因为它们不会立即被新刺激所覆盖。
结果是一个感觉被编辑而不是组装的程序化体验。即使没有固定的剧本或预定义的序列,Wardrome仍然保持着一种进展和意图的感觉。玩家看不到编辑者的手,但在没有死时间的情况下、在未解决线索的有序回归中,以及在故事的整体节奏中感受到它的存在。这是从电影转化为系统的编辑:无形的、结构性的和必要的。
每次游戏中的导演之触
将电影导演原则引入游戏设计是关于创造共鸣——让玩家感受到故事的节拍,强烈程度如同他们在观看一部伟大的电影,同时又增加了互动的沉浸感。从视觉构图和控制节奏到情感框架和环境叙事,我们看到游戏可以采用所有这些技术,尽管通常会有一些变化以尊重玩家的自主权。
现代作品如最后的生还者、内部和死亡搁浅证明,当做得好的时候,游戏可以唤起与电影相同的情感和美学力量,同时提供独特的个人体验。
通过Wardrome的RIDLEY系统,我们试图进一步推动这个想法,将一个虚拟的“导演”嵌入游戏的人工智能中。RIDLEY不仅仅是运行游戏世界;它进行剧作——根据玩家的反应调整角度、时机、语气和叙事焦点。我们的希望是,这将使每个玩家的故事感觉紧密导演但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一个玩家可能无意中创造出一个缓慢展开的政治惊悚片,另一个则创造出一个充满动作的太空史诗,纯粹是通过RIDLEY安排他们的游戏叙事的方式。
对于游戏开发者来说,关键在于电影原则并不是将游戏变成被动电影——它们是关于利用电影语言来增强互动体验。即使是一个程序化的、系统性的游戏也可以受益于导演的触感:深思熟虑的构图以突出关键时刻,尊重玩家情感旅程的节奏,最大化影响的视角转换,以及从每个角落低语传说的世界细节。
通过研究电影技术并创造性地将其映射到游戏系统,我们打开了叙事的新可能性。毕竟,无论是在剧院座位上还是在电脑前,人类玩家渴望难忘的故事和情感旅程。工具和媒介可能不同,但伟大导演的原则——清晰、意图、与观众的共鸣——仍然是普遍的。
在Wardrome中,这些原则指导RIDLEY AI创作出一个回应你并让你感受的太空歌剧。我们很高兴看到玩家们踏入这个有指导但又开放的体验。凭借一点运气(和大量的迭代),RIDLEY的无形之手将确保从Wardrome中涌现出的故事与任何剧本传奇一样引人入胜和富有电影感——而你,玩家,会感觉自己既是英雄又是自己科幻史诗的共同导演。